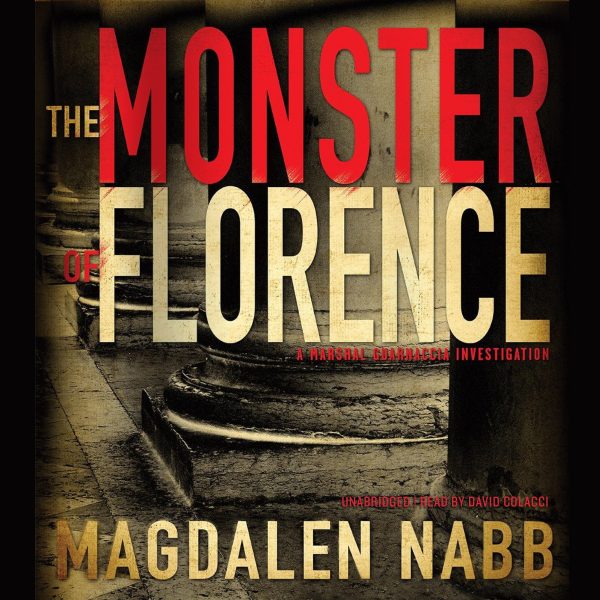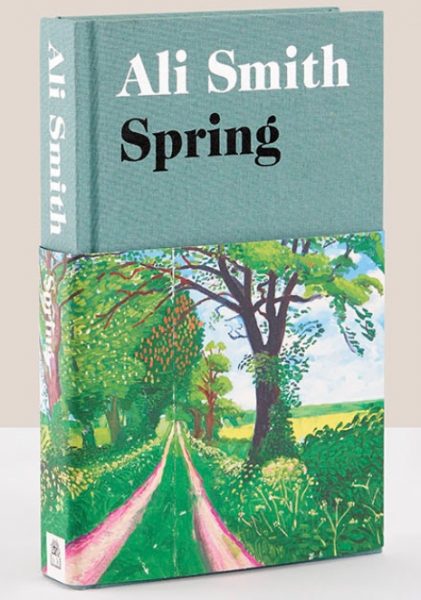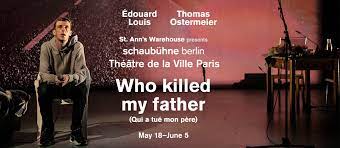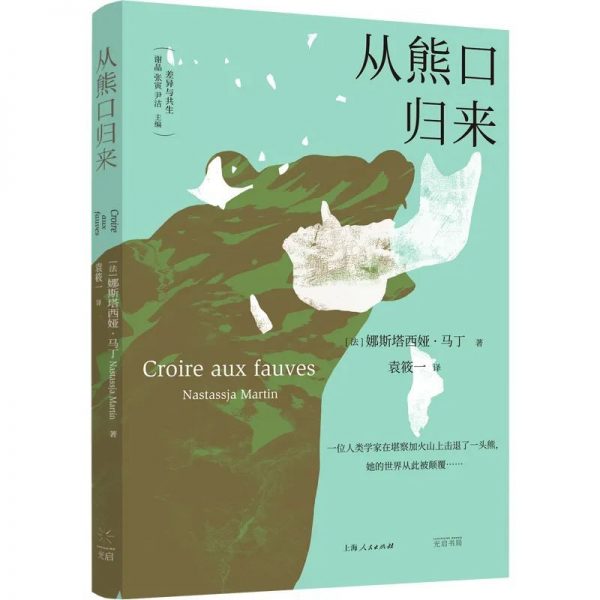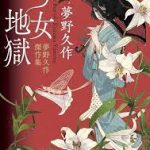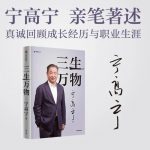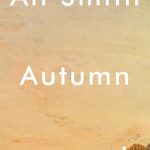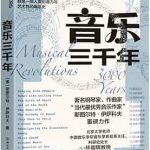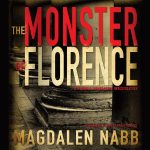石黑一雄的小说《长日将尽》(1989)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。该书出版当年荣获布克奖,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。它探讨了记忆、遗憾、尊严,以及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对身份与意义的追寻。作为一位拥有日本血统的英国作家,石黑一雄借由一位年迈的英国家仆史蒂文斯的视角,展开一段既个人化又充满政治隐喻的旅程。本文不仅评论小说的艺术成就,也深入其文化内涵,并在日本文化、传统中国价值观以及西方文化之间展开对比性讨论。
文学评价
从表面上看,《长日将尽》讲述的是一段关于失落与错失的旅程。史蒂文斯驱车穿越英格兰乡村,表面上是去拜访昔日管家肯顿小姐,实则逐渐沉浸在对过往的反思中——对其在达林顿庄园的服务生涯,以及他曾深信不疑的“尊严”、“忠诚”和“专业”。
小说最受赞誉的特点在于其叙述风格。石黑一雄采用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者——史蒂文斯,其语言克制、形式严谨而情感压抑,形成强烈的戏剧反讽与情感张力。读者常常在史蒂文斯意识到之前便已察觉,达林顿勋爵其实是个亲纳粹的政客,而他对肯顿小姐含蓄却始终未表达的情感,也成为深埋于岁月与自我压抑之下的一段遗憾。
小说因此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叙述,更是对“盲目忠诚”的质疑。史蒂文斯引以为傲的“尊严”,最终被揭示为一种将其与真实情感隔绝的面具。在小说最后的码头沉思中,他终于觉醒,但为时已晚。
特别视角与文学意义
除了普遍关注的情感压抑与错失主题外,《长日将尽》也可被解读为一部关于后帝国怀旧情结与服务神话的沉思录。史蒂文斯对职责与等级制度的执念,象征着一个拒绝面对自身衰落的英国。
他的旅程如同英国自身的命运隐喻——一个逐步认识到其昔日“伟大”或许只是虚幻,甚至是危险谎言的过程。这一层次的解读使史蒂文斯不仅是个人悲剧角色,更象征着一整个阶级和时代的幻灭。
另一个值得注意却较少讨论的维度,是小说的语言质感。史蒂文斯的语言克制得近乎干涩,但也正因如此,读者得以在字句间的空隙中感知情绪。这种叙事“沉默”不仅是风格的选择,更是一种道德拷问:那些被隐去的内容,为何被忽略?
日本文化影响
尽管石黑一雄5岁便移居英国,他仍承认日本文化深刻影响了其作品的情感结构与叙事方式。日本传统重视荣誉、忠诚、自我克制与体面,这些在史蒂文斯的“尊严”观中均有体现。他的行为近似于日本文化中“义理”(giri)与“人情”(ninjo)之间的冲突。
小说中的沉默与隐喻,也可与日本美学——如俳句、能剧等——中的“留白”呼应。石黑一雄将这种东方含蓄叙事成功移植于英伦背景,创造出一种跨文化、含而不露的文风。
中国文化共鸣
《长日将尽》中亦可见中国传统价值的影子。儒家讲求的等级礼仪、忠孝观念与情感克制,在史蒂文斯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中,主人公为道义牺牲情感乃至性命,并被视为美德。
但两者差异在于,传统中国叙事往往给予牺牲者以社会或道德上的正面回报,而石黑一雄却以批判态度描绘史蒂文斯的“忠诚”——当这种忠诚脱离伦理和情感时,它不过是空壳。
此外,中国文学中常有“天命”作为道义与正邪的平衡机制,而石黑一雄却不给读者任何“宿命的正义”作为慰藉。史蒂文斯既不被惩罚也不被拯救,他唯一的归宿,是向自我坦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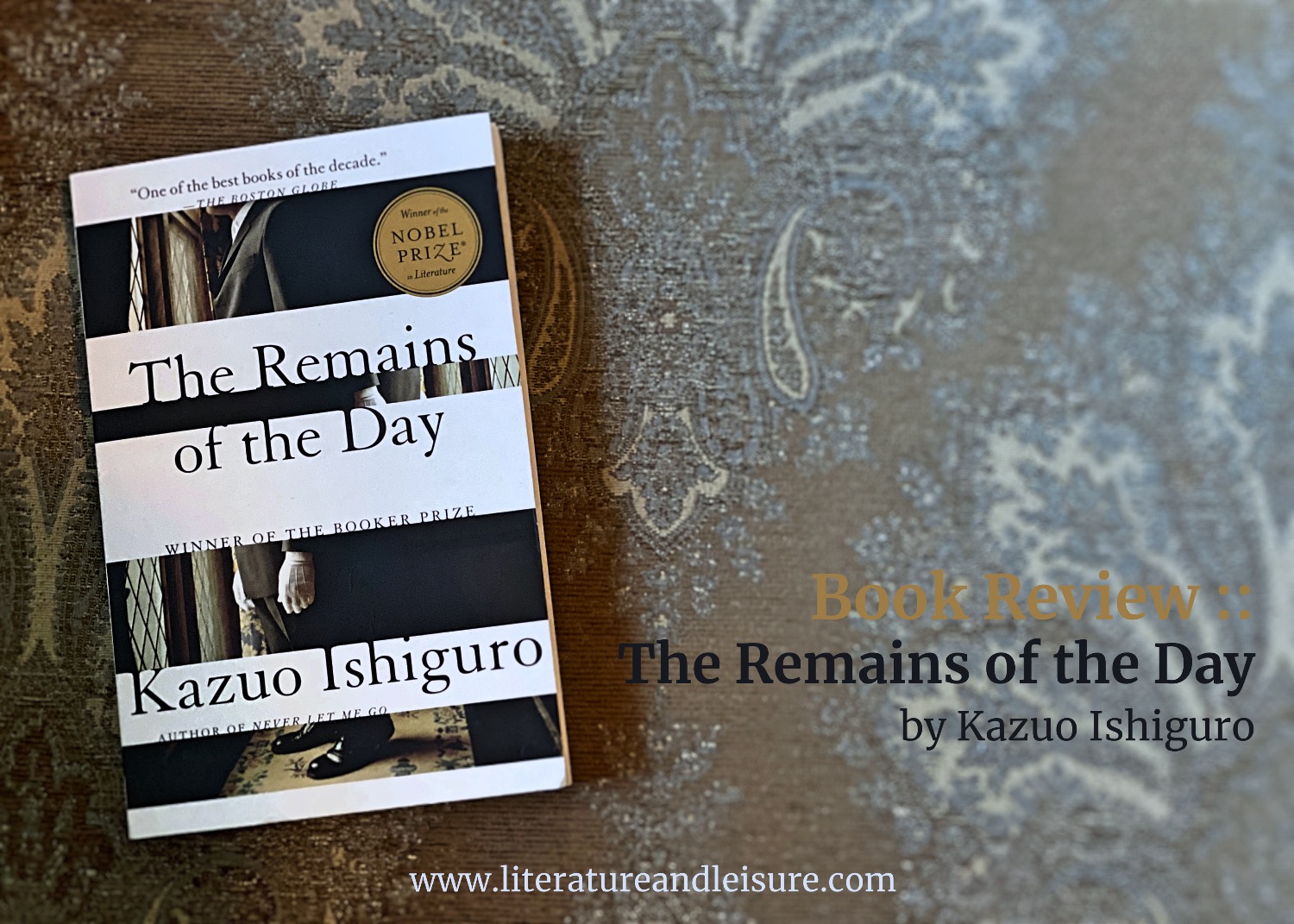
西方文化语境
在西方传统中,史蒂文斯是一个熟悉的角色。他如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、霍尔顿·考尔菲尔德或哈姆雷特——都是在内心欲望与社会角色之间挣扎的人。
西方批评家多视《长日将尽》为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反思,无论是帝国主义、贵族理想,还是“高尚仆人”的神话。与东方强调群体责任不同,西方文化更重视个体意识的觉醒。在这种语境下,史蒂文斯的觉醒或许是一个“微小的胜利”,但它的代价是无法回头的孤独。
结语与推荐
《长日将尽》是对人生意义、身份选择与情感压抑的深刻反思。它不是那种情节起伏的小说,而是要求读者慢慢体味,静静聆听。它不是关于一个管家或一段历史的故事,而是关于每一个人的选择与失落。
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会从中看到不同的影子。对于信奉等级与责任文化的读者,它可能是一面镜子;对于强调自我与觉醒的读者,它更像是一个警钟。
最终,这本书问的不是“他是否忠诚”,而是:“忠诚值得吗?”它质疑的不是过去的荣光,而是我们如何面对如今所剩无几的“余晖”。
写给读者的最后一句话
如果你曾怀疑过自己是否走错了路,或曾疑问理想是否值得倾尽一生,那么请慢慢读这本书。让史蒂文斯的声音引导你。当你合上书页时,也许会轻声问自己一句:我人生的黄昏,还剩下什么?